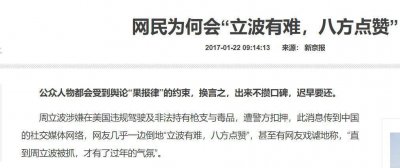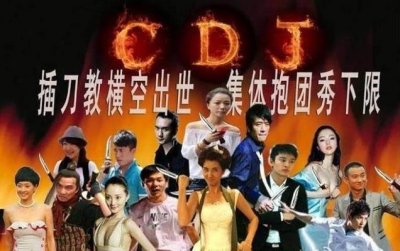王立铭:跨时空对话薛定谔|访谈


王立铭,80后青年科学家,曾先后就读于北京大学、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担任过研究员,现为浙江大学生命科学研究院教授、博导,获得过2015年度“求是杰出青年学者奖”。
除了科研学术上的建树,王立铭还是生命科学领域的科普达人。他的著作《吃货的生物学修养:脂肪、糖和代谢病的科学传奇》获得过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网络课程《生命科学50讲》《众病之王的解决方案》等,收听人数超过10万。
眼下,王立铭出了新书《生命是什么》。70多年前,奥地利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薛定谔写过一本同名书并将“生命是什么”的疑问留给世人,那本著作被视为“20世纪的伟大科学经典之一”。今天,中国青年科学家向薛定谔致敬,并对这一问题给出了当今时代的理解。长江日报读+周刊专访王立铭,试图描摹生命的科学样貌,也试图找寻生命科学技术突破与伦理道德底线坚守之间的平衡。
两本《生命是什么》
生命是什么?这可能是一个最简单的问题,也可能拥有最复杂的答案。1944年,物理学家薛定谔突然闯入生物学领域,出版《生命是什么——活细胞的物理学观》,尝试揭示生命进化里的遗传微观奥秘,在20世纪石破天惊。然而,基于时代局限,薛定谔这位量子力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对于生命的认识并不透彻,他并不知道遗传物质DNA(脱氧核糖核酸),还以为生命就是蛋白质的反应。
将新书取名《生命是什么》,王立铭直言不讳,“是致敬我的偶像薛定谔,更是试图回答他70多年前提出的这个问题”。
对于薛定谔的《生命是什么》,王立铭评价,“那本书在科学史上很重要,但它的重要性其实不在于揭示了多少生命现象的奥秘。薛定谔很睿智,但他仍是一位物理学家,他对于生命现象的观察仍是一个外来者的身份。所以,与其说薛定谔讲出了多少人们没有挖掘到的新发现,倒不如说他为人们认识生命现象提供了一个新视角,最核心的观点,我觉得在于薛定谔抛出了一个声明——生命现象再复杂,都不可能超越物理、化学定律所规定的边界。”
时代变迁,科学进步,隔空回答薛定谔的问题,王立铭说,“我们对于生命现象的理解已远超薛定谔时代。但对比两个时代,我觉得有两点特别有意思。第一,尽管我们发现的生命现象的细节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但薛定谔那个声明还是对的,他的思想非常有洞察力和指导价值。第二,在薛定谔这个原则性声明的框定下,我们这个时代对生命的理解,在各种尺度上,从细胞的尺度、组织的尺度,到个体的尺度、智慧的尺度、群体的尺度等,都取得了非常惊人的成就。我写这本书,也是试图从这两个方面回应薛定谔。”
生物学家应该关心的事
除了薛定谔这位物理学家,另一位物理学家杨振宁也深刻影响过王立铭。高二时,王立铭翻起一本杨振宁的随笔集,谈到自己投身粒子物理领域的原因,杨振宁写道,“一个年轻人在研究职业开展的早期进入一个蓬勃发展的学科,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
受物理学家的影响,为何没有进入物理学领域?世纪之交,社会舆论呐喊着“21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在当时的王立铭看来,生命科学就是蓬勃发展的学科,时代在召唤。他最终也如愿考入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后又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深造并取得博士学位。2015年,王立铭获得“求是杰出青年学者奖”,巧的是,这个1995年设立、专门奖助在中国内地从事基础研究领域的优秀青年科研人员的奖项,由5位科学家共同倡议设立,其中就有杨振宁,另外4位则是陈省身、周光召、李远哲、简悦威。
听过王立铭的课程,或是关注过他的微博,与他聊过天,很容易发现这是一个思维和语速极快,善于表达且不失幽默的人。他喜欢表达,也喜欢文学,在选择生物学之前,他甚至认真规划过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或历史系,因为迷恋《红楼梦》,他甚至想过当一个“红学家”。对文字的擅长与热爱,使得他的科普著作深入浅出,通俗易懂。雨果奖得主、《三体》作者刘慈欣为《生命是什么》作序时评价,“首先是视角广阔,从生命的起源到自我意识,从分子生物学到社会学,使读者对生命科学有了一个全景式的了解。其次是本书明晰而生动的叙述,真正把生命科学作为活的科学展现出来,让读者感受到了生命的神奇与诗意”。让更多人认识并理解科学,并不是一种“不务正业”,相反,为公众消弥误解、击碎谣言,是一件至关紧要的事。
观察人和社会,在王立铭看来,也是生物学家的职责所在。“生物学家本质上关注的是生命现象,而生命现象本身是跨越众多尺度、众多层次的一个复杂性问题。”王立铭认为,“通过这本书写作的逻辑,我也在试图说明一件事——生物学家在理解生命现象的过程中,实际上采取的措施也是多尺度、跨层次的。我们除了想理解生命的物质基础,我们也关心个体的相互作用,智慧的形成,甚至社交、自我意识、自由意志等。生命现象既然如此,生物学家就必须关注这些。”
【访谈】在生命面前,科学既要谦卑也要自负
幸福感是人类所拥有的非常偶然、非常独特的事情
读+:郝景芳(雨果奖得主、《北京折叠》作者)为《生命是什么》作序时说:“我们生于幸运,幸存于幸运”。您在书里写,在生命的演化、智慧的形成、死亡的降临上,人类其实都没有话语权,一切都是“偶然”,充满了无可奈何,您觉得这种偶然能称为幸运吗?
王立铭:偶然和幸运,这两个词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很多物理学家也会思考,假如有任何一个基本的物理参数发生一丁点变化,比如,万有引力常数发生了变化,基本粒子的重量发生了变化,那么,我们今天这个宇宙,这个地球,今天的生命,很有可能不复存在。生物学家会从另外的角度思考同样的问题,地球的化学构成、温度、大小,地球周围有个月亮等,这些所有史诗级的事件,如果有一个稍微发生点意外,那地球上可能压根儿就不可能出现生命。所以,地球上会出现今天这样的生命形态,会出现人类这样的智慧生命,本身是一件极端稀少、非常偶然、十分幸运的事情。
读+:从生命科学的角度理解,您认为幸福的内涵是什么?
王立铭: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实际上我们很难说这个所谓的幸福感,到底是进化史上非常久远的事情还是短近态才形成的,这无法考证。其他比人类简单一点的生物,它们没有智慧思维,更无法验证这些生物是否有所谓的幸福感。我个人的观点,大概率是没有的。因为绝大部分动物并没有自我意识,它都不知道自己是谁,当然就谈不上做出一些自我感觉幸福的声明了。你可以把它们理解成一个由各种反馈机制构成的“机器”,是为了满足某些目标而存在,比如生存、繁殖。
相较而言,至少人肯定是有所谓的幸福感。从人类文明产生、发展到现在,无数人讨论过幸福这个话题,到底有没有能够客观定义的幸福指标,有没有寻找幸福的方法论,幸福是虚妄还是真实存在……从科学上讲,没有谁对谁错。对我而言,可能我有一点科学家的视角,我觉得在满足生存和繁衍的本能之外,能够主动探寻一些与世界相关的秘密,能够发现一些可能在40亿年进化史上没有任何生物意识到的现象和规律,那我觉得,这就是非常幸福的事。因为人类的这种能力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偶然、非常独特的事情。
读+:有一个流传已久的说法,绝大多数人的大脑只使用了3%,如果人脑使用率达到100%会是难以想象的事情,但近期又有研究表明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对于人脑的利用率,生物学上是否有定论?
王立铭:说人的大脑只使用了百分之几,这是一个流传已久的误解,或者说是谣言。
首先,现在已有证据表明,人类大脑所有的脑区都至少在某些人类研究过的活动中是非常活跃的,现在还没有发现人类的任何一个脑区在所有活动里都保持沉默,只不过各脑区活跃的所需条件和时间不一样。比如说海马区,这是一个和学习、记忆相关的脑区,它在学习、记忆的过程中非常活跃,但可能在别的活动过程中相对不活跃。
其次,大脑是一个非常昂贵的器官,成年人的大脑重量大约是三磅(一公斤多),只占人体总重量的百分之几,但大脑的能耗非常大,大约占据了人体总能耗的10%到20%。从进化和生理角度衡量,很难想象在进化过程中,人会专门保留一个如此昂贵但实际利用率极低的器官,难道就是为了留给现代人开发它?这是不可能的。大脑的利用率如果真那么低,早就在进化过程中被淘汰了,至少那部分没被使用的脑区会被淘汰。所以,它既然一直存在,一定是有非常重要的生物学意义。
读+:在宇宙中,生命是个大概率事件吗?所谓的地外生命,真的存在吗?或者说他们的“生命”和我们的“生命”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吗?
王立铭:生命和智慧出现的可能性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我没法给出什么答案,甚至无法给出个人化的猜测。
一方面,我觉得宇宙中应该还有更多的星球孕育生命。一个最简单的出发点是,地球上出现生命是很久远的事情,地球形成于46亿年前,现在已有证据表明,地球生命可能在38亿到40亿年前就已经出现了,而那个时候,地球的生存环境仍然非常恶劣,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地球上的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包括温度、水陆环境、海洋、大气成分等。但洪荒巨变之中,生命的形态一直随之变化,一直顽强的存在。因此,我觉得生命应该有足够的可塑性,能够出现在各种各样的宇宙环境中。宇宙太大了,恒星和行星不计其数,如果计算概率,我们可以比较安全而乐观地推测,宇宙中与地球环境类似的星球应该非常多,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生命是可能性非常大的事件。
但另一方面,宇宙中是否还有像人类一样的智慧生命,我个人就没那么乐观了。当说到其他智慧生命的时候,我们隐含的问题是,地球文明到底有没有可能和宇宙中的其他文明进行交流?这一点,我比较悲观。原因在于,回看人类的进化史会发现,虽然地球生命出现得很早,但智慧生命的出现处于非常晚期,过去20万年才出现了智人,而后,在1万年短暂的时间内迅速建立起高度发达的人类文明。文明的出现,只占地球生命演化史的几万分之一,智慧生命是一系列极端稀少的巧合综合而成的产物。以这个标准衡量的话,其他星球上会不会出现智慧生命,这很难说。
更何况,地球智慧文明,也就是人类文明相对于宇宙时间而言,目前还非常短暂,非常年轻。我们其实没有经验和信心去预判一个智慧生命建立的文明可以持续多久。一万年?十万年?百万年?还是更长时间?很难说。那么,在浩淼的宇宙当中,如果智慧文明持续的时间相对短暂,不同星球的智慧生命能不能在时空上恰好重叠,同时存在好几个,这是一件很可疑的事。再考虑宇宙特别广袤,如果人类的物理学是正确的,那星际文明之间的交流也不可能超过光速,在一个智慧文明存在的时期,它是否有足够的时间和其他远距离星球的智慧文明进行交流,这是另一件挺可疑的事。
但有一点,不管是薛定谔那本《生命是什么》,还是我这本《生命是什么》,实际上都在讨论同一件事,就是不管生命具体的形态如何,什么物质构成,什么组织形态,它都必须在一定的物理、化学框定的边界内才能存在。比如说,生命一定需要能量来构建秩序,一定需要某种形式的遗传物质来传递遗传信息等。如果有一天我们真的发现了地外生命、地外文明,我想,这个地外生命跟地球生命会大同小异,很可能他们的底层规律是大致相同的。
当科技与道德发生碰撞,胜负绝非一概而论
读+:您在前言里说,在人类所有的科学领域中,生命科学是最谦卑、也是最自负的一门科学。您对人类未来的设想是做“生命的主人”,这会不会过于自负?
王立铭:谦卑和自负,这是生命科学的有趣之处。我想表达的意思是,所有生物的生存和繁衍都要遵循自然选择的规律,所以本质上,人类在自然选择的力量面前,都得保持谦卑。但从另一个角度衡量,自负是有道理的,当然,这可能也有点人类中心主义思想。不过,事实上,人类确实可能是这个星球40亿年生命演化史里,第一种,也是唯一一种有条件摆脱自然选择的物种。比如,我们发明了药物,让很多原本活不下来的人可以生存,我们发明了各种科学技术,发明了各种各样的国家机器……归根到底,人类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生存和繁衍摆脱自然选择的目标,而这个目标在40亿年里从来没有被其他生命实现过。从这个角度讲,我们是有理由为自己骄傲的。如果没有近代科学的发展,我们大概率不会在这里讨论这个问题,因为很可能我们根本就不会出生,也很可能我们一出生,在成长时期就因为各种各样的疾病,因为缺乏食物,因为自然灾害等就死掉了。
顺着这个思路继续推演,很容易意识到,人类既然已经开始利用自己的智慧尽可能地摆脱自然选择,并让更多人活了下来,活得更好,那么人类一定会继续做这样的事。我们最终可能会通过修改自己的遗传物质,让人类能够具有更好的生存、繁衍以及控制世界的性状。这看起来是一个不可避免的未来趋势。因而,人类也确实要对自己的自负心理有所警惕,那就是,我们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去影响自然选择的路径,去对抗自然选择对我们的影响,从而让人类能够获得更轻松、更好的生存机会,这是需要我们时时考虑、反复掂量的事情。
一句话总结——我觉得,人类有理由自负,但也恰恰因为人类容易自负,我们可能需要警惕自己是不是过度自负。
读+:迈克尔·桑德尔的《反对完美》中谈到了很多和基因技术相关的社会公共议题,您会担忧技术失控吗?
王立铭:我首先为技术进步而感到骄傲。自启蒙运动以来,科学和理性的进步带给人类更多的是幸福。不相信这一点的人,他必须意识到,如果没有这些进步,那么他大概率是没有办法在世界上生存的,因为他可能会死于在进化史上习以为常的各种疾病和自然灾难。所以,我首先是一个对技术进步很乐观的人。但技术会不会失控?就像世上所有东西一样,不管它本身具有多少好处,失控的可能性都存在。可是,失控的往往不是技术本身,而是掌握和使用技术的人类。所以我才一直要说,我们有理由自负,但也要保持警惕。
读+:在生命的演化过程中,基因的交换、改变、突变等发生过无数次,为什么人类会在这些问题上产生伦理道德感?这种伦理道德感会限制还是促进人类成为“生命的主人”?在生命技术的发展进程中,曾经多次“突破”了人类的所谓伦理道德“底线”,但好像最终的结果都是技术取得胜利,这是生命科技发展的常态吗?
王立铭:这个问题略有些敏感。人为什么会形成所谓的道德感?如果站在进化论的角度,一个自然的推论可能是,道德伦理肯定在历史上帮助了人类的生存和繁衍,所以它才会顽固地持续下去,比如,某些婚姻的禁忌,限制同类相残等。
但我们也必须意识到,自启蒙运动以来,人类科学技术发展的速度是史无前例的惊人,远不是进化尺度可比的,我们在几百年的时间内就重新塑造了高度发达的文明。相较而言,人类的道德感无法适应社会的变化,这可能已经是,并且会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人类文明的常态。因为,道德感形成于更长时间尺度的优胜劣汰,而人类社会的现状是,经常会被科技爆炸、被科学和理性的高速发展重新塑造。在过去几百年里,那些能够帮助人类提高生活水平,提高生存质量的科学技术,比如抗生素的发明,公共卫生系统的建立等,不管当时有多少伦理道德的反抗,它最终都会成为人类生活的一部分。因为人类和所有其他物种一样,生存和繁衍的本能是难以磨灭的。举个具体的例子,试管婴儿技术刚出现的时候,也有很多人基于宗教和伦理的缘由进行反对,但这项技术本身确实帮助了人类提高生存质量、繁殖后代的质量和后代生存的质量。基于这个简单朴素的原理,最终,试管婴儿在今天已经成为了现代生活的一部分。
科学技术和道德伦理之间产生矛盾并不奇怪,但要说谁应该胜出,这倒很难一概而论。我个人认为,需要就事论事来判断,在具体事件上,衡量哪些科学技术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对人类是有益的,哪些是有害的。我不能说科学技术总是应该胜利,也很难说道德伦理就总是应该胜利。
未来,人类还会不断有新的科学技术来帮助提高生存和繁衍的质量。只是,在那天真正到来之前,我们需要非常审慎,非常小心,一定要做好制度建设和风险评估。
【编辑:周劼】